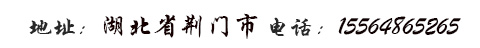Hello,校服先生
|
本文作者:曹周鹏感谢供稿!我所出生的小村庄在中国东部平原,名叫曹集,就是曹家人聚集的地方,整个村子都姓曹。隔壁有个张集,里面却住着很多姓赵的。 那个平原交通便利,铁路公路运河四通八达,夏天种水稻,冬天种麦子。在铁路公路之间散落着无数村子,起名相当凑合,王八坑子,赵家沟子。 当然,最多的还是张集,大张集,小张集,名字相当随意。和那里人的名字一样随意,张勇,赵亮,李军。 当然,更小的孩子的名字更随意,男孩就叫猫蛋,女孩就叫毛妮,至于是毛还是猫,我老家方言很多读音大部分人说了一辈子也没见过对应汉字。我甚至怀疑只有读音没有文字。 所以我有好几个堂兄都叫猫蛋,大猫蛋,二猫蛋。其中二猫蛋又分为大二蛋,小二蛋,还有很多堂妹叫猫妮,大猫妮,二猫妮,三猫妮。 曹集村里有一座山,几十米高的小山包,山上从前是座和尚庙,据说是印度和尚,以前人有病有秧都找它。 后来土改变成小学校,距离我家几十米,我直到读大学才知道苏轼来过我小时候经常撒尿的那个小山包。 对,就是北宋大诗人苏东坡,他曾在我们那个地方做官,来过我们家几十米远的那个叫桓山的地方游览,苏东坡任知府时,曾多次游桓山,并留下10余篇诗文以纪其事。 但是这些和我们村里人没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苏轼是谁,只有读过书的小孩知道苏东坡是谁,但谁也无法想象苏轼这样的大人物会和我们这个小村庄有什么关系。 而且我们根本不知道那座土山叫做桓山,这么平凡的小山包不配有名字。我们村里人没有给它专门起过名字。 但是每个村庄都有一个傻子,每个傻子都有自己的名字。我们那个村庄也有一个傻子,叫做大憨曹。 但是我们那个村庄的傻子和其他村庄的傻子不一样,我们村庄的傻子戴着一副眼镜,没人能想象一个傻子会戴一副眼镜,但是傻子一旦一直戴着眼镜,村庄里的人都觉得很正常,只有外村人才觉得奇怪,傻子需要戴眼睛吗?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傻子都戴眼镜,遇到不戴眼镜的傻子觉得那不是正常的傻子。傻子每天站在马路旁对着空气嘴里骂个不停,他已经成了那个村庄的地标,人人都知道的人物。 我每天上学都路过傻子家门口,傻子无论刮风下雨像一棵树一样站立在家门口对着空气骂个不停。 有人说他因为大学的时候犯了事被打的发了疯,还有人说他在北京被人给开除了,所以神经错乱,有人说他是精神病,还有人说他是神经病,我直到中学才区分出这两个的不同。 憨子叔刚开始每日在村口辱骂,后来民兵队长和村支书镇压过他好多次,他终于被迫改在自己家门口辱骂,再后来民兵队长下岗了,村支书去包煤矿了,就没人管他了。 他风雨无阻,每天九点钟准时出现在家门口辱骂。至于骂的是什么,我曾经好多次驻足侧耳倾听,没有听出来他在骂什么。 我们那土话叫傻子为憨子,每个学校也有一个憨子,也就是总有一个比较憨的学生。我们学校的憨子叫做小憨曹。我们村庄的憨子正是他的叔叔。 小憨曹的憨和他叔叔的憨并不一样,小憨曹并不是憨,他脑袋正常只是不太聪明从不学习却很老实话不多,人人都可以欺负他,他也不吱声,也不还手,看起来很憨,一旦被人取了外号就很难改掉。我也不知道是有人先给他取了小憨曹的外号他才变憨的还是他先憨的然后别人才给他取了外号。 胡萝卜就是他带给我吃的,那时候我刚转学到学校,正好坐在他旁边,还不知道他憨,所以吃了他的胡萝卜。 他总是穿着一身校服,校服胸前很脏,脏灰使校服板结变硬,好像穿着盔甲。每次跑操,他几乎是全校唯一穿校服的。他的一身绿校服异常显眼。 小憨曹上课从来都不听讲,上学和坐牢一样,坐在课桌上浑身难受。夏天的时候他不洗澡,他喜欢用手搓身上的泥,指甲盖刮下来搓成球排在桌子上,手快的话搓完十几个,就下课了,有些课很枯燥总盼望他搓泥丸搓快一点,搓完了就应该下课了。 冬天的时候身上的泥搓不动了他就发呆,无聊的时候搓头发,教室窗户外的阳光打下来,他用手指用力一搓头皮,头皮屑像雪花一样纷纷飘下,薄薄地铺满整个课桌,那一刻和冬天下雪一样美。 我并不情愿和他做同桌,我怕我也被连累被人欺负,但是我吃了他的胡萝卜,也不好不理他,后来发现和他做朋友最舒坦,我可以欺负他而不用担心他欺负我。 我想讨老师喜欢,上课就假装认真听讲。有一次我看他在课本上写着什么,一满整节课都在写,下课了我一把抢过他的课本,上面是我的名字,被他写了满满的好几页,工工整整的印刷体字。 他说之所以写我的名字是三个字的正好写满三页,写完三页正好下课。我说小憨曹也三个字,他夺过课本没有说话。 后来他写的越来越熟练,写完三页还是不下课,课堂上的时间越来越漫长,我们都怀疑学校把时间故意调慢长了。 后来一放学我们就去看火车,我们都喜欢看火车,坐在铁轨旁看火车,他说火车上有坦克,以前有坦克路过。 我们每次都等好久,我们还商量着向遇到路过的坦克敬礼并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了好久。铁轨上驶过了好多火车,绿皮的,黑皮的……可就是一次也没等到坦克。 我问小憨曹在学校为什么不和同学说话,他说他和学校里的同学好像隔着一堵墙,每次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总是得跳起来说,但他的话还没说完,他就落下来了。 我看着他那脏兮兮的校服袖子,无言以对,感觉这样高级的比喻不是一个农村娃子可以说出来的。 我们实在无聊就比赛看谁先跑到铁轨对面,那时候铁路上有四五道铁轨很宽,主要是翻越铁轨需要先聚精会神地听有没有火车经过,那时候的火车有些开得快有些开得慢,但是火车来临前动静很大。 小憨曹胆子很大,他趴在地上用耳朵一听,说火车一会儿要来了,是慢车,比不比赛一把? 我大部分时候都不敢比,我怕跑到中间被火车轧死,只有在我确定没有火车来的时候才能赢他。 我回家后问嫏宁(方言,就是我的姥姥),火车上有什么?嫏宁说装了猪尾巴,是给老毛子还债的。我问二姨火车上是不是也有坦克,二姨说坦克是开往北京的。 后来我坐火车出去读书,再后我坐火车来回去看嫏宁,嫏宁正在太阳底下晒寿衣,她给我展示她那些华丽的寿衣,好像一个女孩子逛街后在炫耀她新买的衣裳。 我说为什么这么早买这些,她说别人家都买了,她这个岁数的人都置办了。我拿起她的寿鞋笑了,那鞋子很小,是特作的。 “跑了好多家寿衣店买不到我那么小的脚鞋。”她说那话的时候脸上带着得意,好像小脚是她这辈子最高于别人的地方最大的成就。 我在村庄的小道上遇到了小憨曹,他已经不上学了,但还是穿着那身校服。 我问他现在在干什么,怎么不上学也不做工。他说瞎逛,沿着铁路瞎逛。他还和我提起坦克,他经常一个人去等坦克,但一次也没等到坦克。 他说老早以前有人亲眼在电视上见到过坦克,就在北京。他的叔叔大憨曹就在北京见过坦克,但没人相信。 我那时每天想着学习想着考重点高中,觉得自己这样的好学生和他这样的人讲话做朋友很没面子,说来说去都是小孩子的玩意了。敷衍了他几句说以后别等坦克了,就急忙走开了。 我最后一次遇到小憨曹是嫏宁去世,他过来帮忙,还是穿着那身绿校服,还是那副样子,那身校服似乎把他给困住了,或者是他把那身校服给困住了。 时间除了让他的瘦小身形在肥大校服下越长越矮壮,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嫏宁去世了我也没有多伤心,她活了将近90岁,对老年人来说足够了。那一次小憨曹没有和我提起坦克,他说他的叔叔,村子里真正的那个憨子几年前就死了,他的眼镜也和旧衣服一起给扔了,是小憨曹偷偷捡回来给藏起来了。 我开玩笑地说我以为憨子叔会像树桩子一样风雨无阻地每天按时出现,永远都不会死。小憨曹说每个人都会死,猫会死,狗会死,人也会死,他还杀过狗。 我听了不说话,村子里没有寿终正寝的猫,也没有寿终正寝的狗,都是莫名消失的,被偷了,被轧死,被药死,被打死,没有人在乎他们是怎么消失的,我的嫏宁也消失了,只不过她是寿终正寝的。 出殡的时候我没看到有人在乎她,那些假哭和鼻涕眼泪也不在乎,我好像也不在乎,风一吹过来,他们就消失了。 我突然感到害怕,我害怕自己有一天也会这样消失…… 我不想消失!我不想消失!我还有很多远大的理想……那一刻我想抱住小憨曹的肩膀却不好意思,那是我第一次想要抱住别人的肩膀。 我那时满脑子都是考试和远大的理想,一心想提前回学校去,他说送送我。 我们抄近路到了我们当初一起等坦克的火车站,他把箱子递给我,我需要私自翻越铁轨到达对面的站台,以前就有人这样抄近路被火车轧死。 我和小憨曹对火车再熟悉不过了,不怕被轧,我瞅准机会一口气穿过四五条铁轨到达对面的火车站台,他在我后面,看着我已到达对面了,他还在四五条铁轨的中间没跑过来。 他的腿脚变慢了,他向我摆摆手返回对面去了,算是送完我了,我看着他转身默默沿着铁路往回走,一辆绿皮车驶过,他急忙躲到了一边。 我站在车站等着车,看着他身穿绿校服渐渐地随着铁轨越走越远,最后和铁轨一起消失在了模糊不清的远方。 后来村子里又出了好多好多个大学生,我也算一个。 这里头却没有一个是考到北京的,都是不值钱的二本,早已没有了憨子叔当年的轰动感。而且村里人早已不关心哪家出了大学生,走出农村已经不是村里人公认的价值观了。 小憨曹在老家养了几十头猪,他20岁时结了婚,十年过去了,校长有了一个十岁的女儿,聪明伶俐,和她父亲一样,写得一手好字,在市重点小学读书。 我在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hongguoxiaofua.com/szxfgm/4933.html
- 上一篇文章: 左耳校服剧照引网友大赞中国式校服逆袭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