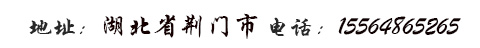Lulurun
| 北京中医白癜风怎么样 https://m-mip.39.net/pf/mipso_5153467.html在08年的秋天,我来到北京,上大学。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是住宿舍的。那时候一切井井有条。那年秋天很热。我总是穿一条褪了色的牛仔裤,一件褐色毛衣,和一双白色匡威。我的头发还很短。我随身带着一个收音机。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好学生。早晨我听国际广播的英语新闻,晚上听国际广播的摇滚乐节目。后来出了一个电影叫《海盗电台》。那里演得真实极了。我就是那样听电台的。熄灯以后我蹑手蹑脚的披上衣服,拿上烟和收音机。在晾衣台上听。男生宿舍那边会传来打闹的声音。还有女生的尖叫。一切都很朋克。秋天的时候我写了一个剧本,叫《乌托邦》,是讲几个小朋友的故事的。这个剧本得到了戏剧社社长的赏识。鬼使神差地,我进了戏剧社。当上了这部大戏的副导,参加一个大学生戏剧节的比赛。真正的故事从这时候开始了。在为《乌托邦》选拔演员的时候,我遇到了陆路。我参与了演员选拔的工作。那天来了很多的文艺小青年。大家都穿着一样的铅笔裤和高帮的匡威鞋,紧身的T恤。他们脸上脆弱又矫情的神情让我感到亲切。陆路在很晚的时候才过来。他的脸很白,头发很乱。他抽到的题目是:公交车上。他表演的是公交车上的星球大战。他在傻气地躲闪子弹的时候我觉得他美极了。他总是心不在焉,格外出神地思索着什么。我注意到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个拨片,陆路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死尸甲演?”然后就走了。陆路成了《乌托邦》的男一号。陆路的出现就像一支大麻烟。此时他只是在我的身体里打开一个口。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当我不以为然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打开了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张开了,所有力量都会走进来。好的,不好的,之后他就不负责地抛下这具张开的身体走开。在《乌托邦》开始排之前,我依然每天听电台,上课的时候去拉屎,在天还亮的时候去教学楼背后抽烟,表面上跟每一个普通的好孩子一样。《乌托邦》开排之后,我就能常常看到陆路。他总是那么可怜,勾着脖子缩在墙角吸食香烟。我总是不知道和他说什么。我们就这样沉默如谜地呼吸。有一天,在我们沉默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们出去租个房子吧。我原来一直跟我女朋友住在外面。但是现在,我们分手了。所以咱们一起租房子怎么样?我们当合作伙伴。”我愣了一下,说:“我考虑考虑。”他笑了一会儿,把烟掐灭回了排练室。那段时间我迷恋一切少年的东西。就是那种微笑的纯净的,奔向希望的少年。陆路是一个少年式的人物,虽然他不是一个让人看到希望的人。虽然他是一个你看到就会觉得要完蛋,要毁灭,完全没有出路的丧人。可不能不承认他让我着迷极了。在陆路提出要跟我租房子,做合作伙伴的那天,同时发生了一件事。我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乐队~就是奇迹一般涌出四个人,凑齐了一个乐队。我的乐队叫zzz,就是喜鹊zhazhazha的意思。我的乐队就像一股暖融融的triphop,带着微微迷幻色彩温暖着我的身体。如果没有乐队,生活的平庸将使我痛苦不堪。这样,顺理成章地,我和陆路一起租起了房子,当作排练室,垃圾场以及一个家。那时我才知道陆路也有一个乐队,组了很久,在圈子里也小有名气。我们的房子在五道口与上地之间,类似于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地方。老房子,很促狭的两居室。我们住在五层,有一个梯子,可以爬到楼顶。幽深的走廊有蚯蚓一般湿的腥的味道,陆路房间的窗户还破了一个洞。我们在大钟寺的批发市场买了红色和蓝色的丝绒布,遮住抹满鼻涕的墙面。在这样的房间里听《丝绒公路》,是很美的事。这样一个锈迹斑斑,颤颤巍巍的老楼是我在北京第一个家。我那时是一个独立的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一个人。我的欲求如此简单。我有一个合作伙伴,一个家,一个乐队,就觉得已经可以瞑目死去。我个陆路的合作很愉快。有课的时候我们都在学校住,装模作样得好像每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周四回家,排练。排练完我们一个接一个爬上天台,喝酒,飞叶子。我们的鼓手总是把梯子踩得吱吱响。我们的家很快就变成一个猪窝。地上横着吉他音响酒瓶,长出苔藓的杯子和脏衣服。我一直觉得那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我处于一个不断被挤压又不断被释放的过程。一切都刚刚好。糟糕的是我和陆路越来越像。我们互相影响,渗透着,以一个非常危险的速度。我们的乐队刚成立,总是跟在陆路乐队后面,给陆路他们暖场。那时候我们总在小D22演出。那儿舞台特别小,但是感觉很好,很酒吧。演出完后其他人都走了,我和陆路坐在D22。那里的酒保都认识我们。我们坐在那里,喝赠送乐队的热啤酒,吃花生米,看演出的视频。陆路是做grunge的,我是做车库迷幻的。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长了,陆路的grunge里有迷幻色彩,我写的迷幻在高潮的时候总有奇形怪状的转音。我们坐到D22开始扫地了,就以一个奇怪的形状搀扶着,缠绕着,一步三摔跤地走回家。我们住的地方很荒芜。到了深夜所有的楼都黑乌乌的只有路灯很亮。有一个通宵营业的沙县小吃。福建人给我们倒蜂蜜水。我们默默地吃小馄饨。青灰的蛾子轻轻地撞击着灯泡,噗噗噗。一切都美极了。那年的冬天很干燥,很温暖。冬天我们听了很多的歌。我觉得好像把全世界的歌都听过了。直至今日,我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当时听过的。我们靠在最大的那个laney的音箱旁。喝着酒,听着歌。这样的时候我总有心里发毛的感觉。高中我做梦都想要这样的生活,好像在那些书里,电影里说的,在房间里开party,抽大麻,和男孩子做爱。我每天穿着校服骑着自行车要去写一本试卷的时候,这些画面就像抽了帧,盘旋在我的脑子里。现在我和陆路过上了这样的生活。但我深深地感觉到我老了。不得不提一首歌。是木马在《果冻帝国》那张专辑里的一首歌,叫feifeirun。这是木马写给他的女人阮菲菲的一首歌。我和陆路在高中的时候都听过这首歌,虽然现在我们和木马成了朋友,在mao我们和谢强坐在二楼喝酒,他没有那么高高在上他也会讲笑话。但是这些都不妨碍我们对这首歌着迷,家里总是盘旋着木马诗人的歌声。我喜欢那句:用我不悠扬的歌声温暖你整个旅程。我总把这首歌改成lulurun。用我合成器上的各种宇宙音弹奏这首歌。陆路总是挂着大傻子一般的笑容说:“真好听。”给我一个保证,让我一直在你身边。那是我跟陆路在一起的最后一段日子。我们都到了一个巅峰,每天晚上都喝得很醉,写不出歌,说不出话。我烦透了那个时候的陆路,他粗俗不堪,他骗太多的姑娘回家,上床,然后甩掉。我常常跟他吵架。吵架的时候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神经病。有一次,陆路和我吃完饭,他在楼道里跟我说:“我不想租这个房子了。”我说:“那你住哪儿?”他说:”平时住宿舍。周末,可以随便找一个姑娘家住。”我没出声。回了家,我把他的效果器摔碎了。之后我把他的木吉他举起来砸。他扳住我的手说:“你不要这样。你神经病么?!”他在这个时候脸上出神的表情更加浓烈。这把我的愤怒推到顶点,我把他的琴砸了,砸了很多下。我们都盯着那把吉他破败的尸体发呆。我有一把和他一模一样的箱琴,Yamahafa,他的琴是漆面的,我的是磨砂。我盯着那把琴想起我们在楼顶上一起弹琴的情景。能看到很多的星星,那些星星让我们觉得民谣比摇滚美。我们的琴包上都贴着luckystrike半个烟盒。我不知道我当时处于怎样一个状态里,好多真气在我的身体里撞来撞去,我的手都抖。这时我看到我的那把琴,悲伤地躺在一堆酒瓶里。我一下就不行了,我开始哭,并且停不住。陆路这时做了一个让我吃惊的动作。他把我推倒了,然后我们就厮打在一起。那种厮打是无声的。那天晚上我们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听音乐,一会儿厮打在一起。半夜停电了,我们就在黑暗里打。四肢缠在一起,把那些痛不欲生的,猛烈的情绪都释放出来。那个时候我有了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太近了,太近了。我们交换了灵魂。我们听了很多遍feifeirun。所有的歌都逃跑了,只有这首该死的歌不停地放。我们把家里一半的东西都毁了。我们都流血了。我们疯了。天亮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我想:我要死了。陆路在天亮的时候问我:“我们还是不是合作伙伴?”我说:“是。”他想了一会儿,说:“可是你越界了。”清晨如此虚弱。清晨如此冷。那次流血事件之后我们没有立即分开。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演出的时候,陆路乐队的一个小歌迷跑过来问我:“你是陆路的女朋友么?”我走了一会儿神,说:“是。”小歌迷眉开眼笑,她说:“我能感觉到。你们的气场就像。刚才你们坐在外面的时候,虽然没说话,但我能特别强烈的感觉到你们的灵魂在交流。”我失声大笑。笑得我的手又开始抖了。我想:陆路,我们他妈都越界了。那是故事第一阶段我和陆路在一起的最后一天。我们喝了好多温吞吞的啤酒。北京下雪了,冬天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雪。我们在D22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陆路已经走了。我撑着支离破碎的头颅回家。陆路的房间几乎没变样。音箱和一把电吉他还在。少了他的电脑和监听耳机。他把脖子上戴的那个蓝拨片放在了桌子上。其他保持原样。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我在潜意识里认为陆路没有走。直到几天后他们乐队的鼓手和我说话:“陆路不玩了。”我才相信他是奔向新生活去了。我没有搬家。我戴上了陆路故意留下的蓝拨片,在那个房子里住过了整个春天。那个糟糕的春天我交到了很多的男朋友,很多莫名其妙的人,有独立制片人,摄影师,摇滚乐手,画画的,甚至有大我十几岁的宇宙学教授。我还在支撑着我的乐队可是我再也写不出歌了。刚开始,我尝试着喝酒,飞叶子之类的方法制造一些幻觉。但是后来这些混蛋的事已经完全沦为了纯粹的混蛋。我依赖这些混蛋,还有我的男朋友们,还有性爱什么的。这些把我的脑子变慢了,把我的脸搞得很混蛋。我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喝酒让我的手总是在发抖,我连弦都捏不准。我跟男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问:“你怎么总是左右摇摆身体?你为什么总是不高兴?”这真该死。我写不出歌,我们的演出越来越少,但我还是愿意去D22,去看一个垃圾乐队的演出。从他们调音一直坐到酒保开始扫地。一切安静的空气都是有毒的。我只有在强大的回授压迫耳膜的时候才能正常呼吸。我当然意识到了自己这种加速爆炸的状态。有一天,我想,我必须得做点什么让自己放松。我在D22和13club旁边的小卖部用公用电话拨通了陆路的手机。他接了。我口齿不清地说:“你回来吧。”电话的那头沉默了一会儿。陆路一字一顿地说:“我不回去。你活得太不健康了。我只想找一个健康的人当我的女朋友。我想做一个正常人。我不会回去。”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我对着嘟嘟嘟鸣叫的“去你妈的!”很奇怪我当时并没有特别痛苦或者特别豁达。我回到D22,要了很多很多酒喝。我坐在那里喝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细节。我想到我们刚住到一起的时候还会在学校住,我在周四的早上回家,他在周五上完课会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我说,在家。他就会傻笑一会儿说,我去找你。想到这个细节的时候我突然心脏疼。那天是浪的演出。很多朋友都在,我不说话在那里喝酒。边远问我“一起去喝酒么”的时候我看到了站在他身后的木马。他戴着那个标志性的礼帽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当时很努力地说:“你唱的feifeirun真好听。”但是说出来是一堆狗屎。我又努力地跟边远说:“我心情不好,我不去喝酒了。”但是我又说出来一堆狗屎。这个时候我无助地发现我说不清楚话了。我烦躁到极点。我对边远摇了摇头。他们就走了。这时我发现木马穿着尖头皮鞋站到了吧台上。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没有注意到他。她优雅地摆动手臂,高唱着“lulurun”木马变成了陆路。陆路带着他五彩斑斓的女朋友站在我的面前。我挣扎着要站起来跑出去的时候摔倒了,头磕在桌子角上,头顶上盘旋着千万的小拨片。我想说:“真他妈的奇怪,一点也不疼。”这次我连狗屎都说不出来了。我晕过去了。醒来的时候我在一间病房里。我脸上插满了管子。我头疼,嘴唇干裂。我惊喜地发现我又能说话了,我清楚地,大声说了一句:“渴……”这时候我病房里站着的两个人扭过头。我发现,那是我的爸爸妈妈。那天我在D22喝到酒精中毒。医院,许多人叫来了我的爸爸妈妈。我差一点就成了一个混蛋植物人。医院躺了一个星期。虽然我浑身都疼,我的大脑好像吊在空中。但是我发现一切都对劲了。我开始清醒起来。我能清醒地感觉到疼,冷,热了。当我可以下床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照镜子。医院的厕所,那儿真脏,很黑,有一股屎味。但我还是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脸。我发现自从陆路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我的脸好像泡在酒精里,浮肿,苍白,混蛋。好像老了十岁。一切都糟透了,只有脖子上戴的陆路的拨片散发着狡黠的光辉。我的额头缝了三针,留下一条蚯蚓状的。我摸着那道疤哭了起来。就在那个又黑又臭的厕所,我哭了很长时间。我的青春我的美丽在这一年没有了,被缝进一个三厘米长的疤里面。我在厕所哭完之后去了外面。我看到了山、树,还有很多湿漉漉的灯。医院的小卖部看到了我曾经很喜欢抽的一种叫做茶花的烟。但是我没有钱买。我隔着玻璃看了一会儿就走了。那是09年的初夏。大一学期末。我带着一颗变慢的脑袋和一道疤回了家。为了静养,爸爸妈妈带着我回了小时候住房房子,在机场,锈迹斑斑,颤颤巍巍的老房子。楼道里有落灰的自行车和一股蚯蚓的味道。我们三热火朝天地重新粉刷了家。我把房间刷成了橘红色,夕阳的颜色,非常的温暖。楼下有一个菜园子,有葱、西红柿、一些花,还有许多树。我走路五分钟就能到我的小学。空气很安静。回了家的第一天我跟我爸爸说:“我想出去买个冰糕吃。”我爸爸给了我十块钱。他不敢给我太多钱,他怕我会买酒喝或者买烟抽。其实我攥着这汗津津的十块钱的时候想过要买一包烟。但是走到一个凉粉摊前面我觉得特别饿。我吃了一碗凉粉。这种饿一发不可收拾。后来我又买了两个冰激淋。前面那段混乱的生活仍在我身体里留下浓重的痕迹。不抽烟的时候我觉得很烦躁,很热。我拿剩下的四块钱去一家理发店剃了光头。那时候我的头发已经很长了。很密很黑在我头顶妩媚地飘动。刚跟陆路在一起的时候我是短头发。陆路说,我喜欢你长头发。我就努力地把头发留长了。现在,一切都没什么意义了。所以我把头发剪了。然后我养成了喜欢摸自己头的习惯,像所有秃顶的叔叔,在头上绕一个圈。回了家,我爸爸盯着我的头看。我羞涩地摸着头站在那里。我爸爸说:“挺好看的。”我又差点哭了。我在家度过了漫长的夏日。我唯一带回家的一件衣服就是在酒精中毒的那天晚上我吐了一身秽物,并且撕了一个大口子的红裙子。我在家就穿小时候的衣服。牛仔裤和拖鞋,还有上面画着微笑米老鼠的小T恤。我爸爸每天和我在家。他在画画,我在晒太阳。有时候我会去楼下给菜和花浇水。有时候我会哼着歌去看小学生放学。孩子们排着队,拿着水壶走。家乡骑着自行车去接他们。我想,那时候我也是这样的,我家离得近,我就拿着双百分的试卷一路跑回家。那时候我没有接触摇滚乐,不抽烟,不喝酒,不认识陆路。多么正直,没有一丝可疑的阴影。我站在那儿看着孩子们。他们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的光头和疤,还有紧绷绷的牛仔裙,像看一个神经病。这种眼神让我不好意思。以后,我就躲在树后面看了。现在要提一个非常久远的事情。就是在我上大学初写的那个话剧。在我和陆路住到学校外面之前参加了比赛,公演了一次,拿了一个非常扯淡的奖。但是后来被魔山剧社的人看中。他们喜欢我写的剧本,在我呆在家的那个夏天他们联系我,并且要求我继续写下去。六月和七月我一直处于一个缓慢恢复的过程。我每天做一些不动脑筋的家务。晒太阳。在家里和街上闲晃。偶尔我还会想起陆路。想起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拿着薯片、报纸和金奖白兰地一起上毛邓课的情景。但是后来的很多事我都忘了,或者说不愿意想。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哼起lulurun,在拖地板或者浇西红柿的时候。刚开始,我一唱起这首歌就头疼,我的疤就像要喷射了一样疼。后来一切平淡了。我的眼泪我的爱,我的魂魄我的美丽的陆路,他在毒辣的太阳下随着那些迷路的酒精从我体内蒸发变淡了。我跟着妈妈吃素食,变成一个淡人儿。八月的时候我又开始写作了。我慢慢地,让自己一点点进入那个美丽的状态里。我写东西不能一点音乐都没有,我就让爸爸从城里的家拿两张碟给我。爸爸给我拿的是,乌仁那的《骆驼的步态》和木马的《果冻帝国》。我看到《果冻帝国》的时候我变成一个果冻,又黏又软,失控地掉进回忆里。我害怕看到这个。看了那张专利两天然后开始听,feifeirun。听的时候我发现少了很多我所预计的猛烈情绪。我像高中时候一样想:阮菲菲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偶尔我会闻到空气中飘来一股药味。那是陆路身上标志性的气味。他有鼻炎,常年用一种苗岭鼻炎灵,他的身体发肤都沾着这种味。我一边写剧本一边走神,我想,他的健康的,温情的新女朋友会让他按时吃饭,他可能已经不再用这种药。我在这个时刻就会摸一摸陆路的蓝拨片,这些让我的心脏剧烈地抖动起来。我在家呆过了整个的夏天。我很平静,偶尔有点小资产阶级的小忧伤。我那会儿不明白这平静只是一个假象,于是我很高兴可以回到一个轨道上。夏末的时候我回了北京。我的头毛茸茸的。我像一年前一样踌躇满志地背着一个牛仔背包坐着火车回到学校。但是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发现没有我的床了。具体点说,我的床上堆满了不属于我的东西。书架上有一本《伤心咖啡馆之歌》伤心地望着我。回到宿舍的时候没人在,于是我的尴尬和惊讶没有目击者。我背着那个牛仔包孤独地在大街上游荡。我就这样走到了D22。这个时候天黑了。我死了。我站在幽蓝的D22门口的时候突然明白了这个夏天的小玩笑。我每天装作心如止水,装作间歇性失忆。其实我从内心是渴望回到这个地方。这个美不胜收的小场所,可以让我一瞬间解放,每一个器官都解放。于是我的脚,这个可恶的器官把我重新带回了这里。我走进去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D22刚开门,小虎在忙碌着把啤酒搬进冰箱。我挑选了吧台角落的一个座位。我第一次在这里有了该死的紧张。那天后来我记不清楚了。紧张了一段时间后我又开始像以前那样喝酒。小虎说我短头发挺好看的。我问身边的一个男的要了一根中南海。我以前很讨厌这种烟,它很复杂,被贴上许多莫名其妙的标签。它让抽烟这件事情变得不那么纯粹美好。但我只能小贩这种烟。我吸第一口的时候差点要晕过去了。那是一种我任何一次喝酒,抽烟,飞叶子,做爱都没有的飞翔。这样的感觉把我晕乎乎地拽回了以前的生活中。太彻底了。我在D22喝了一些啤酒,抽了烟。得到一个不太好的消息joyside在夏天的尾巴上解散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是边远的好人脸。他身上那种植入式的王者光芒会不会一瞬间就熄灭了。我从D22出来一路迤逦着回家。没错,回家。潜意识指使我走回和陆路的房子里。钥匙放在一个破花盆下面。我和陆路总是喜欢丢东西,所以只要一出门就会把钥匙放在那里。我从破花盆底下掏出钥匙。进了门。我毕竟还是醉了。那两个月的健康生活让酒精在我身体里留下的性格淡去了一些。早晨我醒来看到房间里熟悉的蓝色金丝绒窗帘觉得这个世界太混蛋了。我又回到这个屎地方。窗帘,酒瓶,音箱,我美丽的鞋都落了灰,伤心的看着我。我太受不了这些眼神。我早晨醒来就匆匆出了门。在明晃晃的街头我绝望极了。我回不了宿舍,又不想回家。D22在沉睡中。我没有地方去了。我给一些善良的朋友打电话,费力地表述着我的情况。终于,有一个男孩,愿意收留我。我跑回家收拾了一些衣服,拿了我的琴就奔向三里屯。我的新生活在一次虚假的回归之后开始了。那个男孩叫蓝精灵。他是一个脆弱的同性恋。他和他的男朋友军军住在三里屯外交公寓旁边的一个小区里。我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我不胜其累地每天奔波于学校和蓝精灵的家里。我的同性恋朋友蓝精灵是一个善良的人。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日子让我再一次得到内心的安缓。他们很脆弱,很善良,很美。军军在金融街工作蓝精灵总是做好饭等着他。他们家的灯是黄色的,很温暖。一切都是静静的。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心灵之间的那种交流。这时候我总是很伤心。我想起陆路。我们曾经也给别人这样的感觉。那些我不以为然的,微不足道的细节在这些时候轻轻地揪着我的心脏。我们吃完饭一起看电视,聊天,抽烟。有时候他们会叫一些朋友来开party。在房子里跳舞。有很多的同性恋。刚开始的时候我有些不习惯。他们抱在一起跳舞。时间长了就会觉得这样很好。是那种很晕的好。每个人之间都很自然地有曾经令我惊讶的灵魂之间的交换。我抱着胳膊坐在沙发上看他们跳舞。身体左右摇晃。一切都像泡在加了整粒蓝莓的苦艾酒里,摇摇晃晃的。九月天还很暖和的时候,我、蓝精灵和军军三人就手拉着手在三里屯的酒吧街上走。三里屯给我和D22不同的感觉。三里屯是上层的,暧昧的,D22是原始的,直接的。那里有很多漂亮的中国人,外国人,路边摆着麻辣烫,假烟,啤酒,英文盗版小说的摊。我们带着很高的肾上腺素去一个叫二楼的酒吧喝酒。酒吧在二楼。老板会给不同的人调奇形怪状的酒。他总是给我调一种类似长岛冰茶的酒,基酒有琴酒和利口酒。好像止咳糖浆。但我总能喝到很醉。从二楼的窗户看出去总是雾蒙蒙的,好像在伦敦。就像我的生活。虽然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仿佛达到某一种平衡,看起来天衣无缝的,但我这部分还是缺失着某种东西。俄国人arty是蓝精灵他们的好朋友,几乎所有的party他都去。他总是拉我跳舞,他说他喜欢我。我对外国人没有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他们很浅。但是arty不一样。他说喜欢我的时候会脸红。他有一张向阳花一般的脸。他让你觉得生活中是存在绝对美好的。有一次他骑着摩托车载我去兜风,那是十月中旬,傍晚微凉。我们从北三环骑到东三环。路过水立方的时候灯亮了。太棒了。好像看到了一整个大海的寂寞。风吹着我流眼泪。arty在呼呼的风中跟我说:“我很喜欢你。你很美丽。你总是像苔藓一样潮湿的。但是你很美丽。”那应该是我最好的时候,我二十一岁。我的美丽被酒精和陆路夺走了。所以当arty真诚地说,你很美丽的时候,我整个身体都湿润了。arty是我在刚上大学的时候热爱的那种男孩儿,是早晨的,奔向希望的少年。那个晚上我坐在飞快奔驰的摩托车上,想嚎啕大哭,给自己一个彻底的解放。但是风吹得我流不出眼泪,我只能轻轻地唱:“用我不悠扬的歌声,温暖你整个旅程,lulurun,lulurun。”我在学校遇到了陆路。和他所谓的正常人女朋友-一个蛆一样的女孩儿在一起,白的,黏软的,腻的。他们站在曾经我和陆路经常吃饭的老马家拉面门口。我已经有五个月没见他了,但是我知道那是他。他剪短了头发,脸很白,他勾着脖子站在那里。我盯着他看。从他的左边走到右边。这件事很无聊,但我当时完全被一个念头支配着,就是让他看到我。他的蛆先看到了我,然后拉扯他的衣服。他扭过头。那个美妙的时刻我的整个身体发肤都被拽起来了。好像我回到北京第一天在D22抽的那一颗中南海。他盯着我,先看我的头,然后看我的眼睛。面无表情。浓烈的药味流动在我们之间。我面无表情地在十米开外的地方小声说:“陆路。”他就转过了头。我曾经想过如果我碰到他和他的正常人女朋友我一定会冲过去扯住她的头发,我期待着一种歇斯底里的同归于尽。但是没有。我默默地走开了。晚上我没有去蓝精灵那里。我回了五道口那边的家。家里还有一些过期的酒和旧叶子。我喝了酒,飞颗叶子。笑得像个大傻子。我们的音箱埽进了雨,刺啦刺啦的响。然后我就饿。买了一大堆薯片和巧克力。吃完后我就开始打扫房子。扫窗帘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这件事让我的脑子嗡的一声。我离开北京之前陆路的窗帘是红色金丝绒,我的是蓝色。站在陆路的房间变成颗蓝色。我走了一会儿神。突然反应过来这期间陆路回来过。他换过窗帘!本来当时我是在一个飞的状态里。那一刻突然清醒了。后来我在房子里又找到了新的拨片等蛛丝马迹。我确定陆路回来过,并且就在不久之前!我在水泥地上坐了一个晚上。白天的时候我决定搬回来。我疯了。早晨我没有上课我直接跑到蓝精灵的家里。我抓住他说了很多遍但都没有办法说清楚。其实这件事本身就让我不清楚。我跟蓝精灵比划了一个早上,蓝精灵还是没有明白。最后我只能说:“我要到一个完全没有人打扰的环境里,把我的剧本写完。”蓝精灵有些失落,他黯然失色的时候很美丽,他漂亮的愁眉苦脸着帮我收拾东西。他说他会很想我。我当时完全沉浸在陆路的情绪里,我只是想我必须很快回去。立刻!就这样我告别了蓝精灵夫妇回到我的痛不欲生的家。生活此时只剩下等待。生活此时只剩下狗屎一般的等待。日复一日地等着陆路的回归。但是回到家里我发现我写不出东西。我每天都很high,晚上不睡,早上也不睡。炯炯有神。但是全部的事情只是等待。写不出东西也不想唱歌,像一个弱智一样等在那里。魔山剧社的人打了很多次的电话来催剧本。其实我只是缺一个结尾。但是我就是写不出来。拿起笔我就像高考那样做卷子,脑子总是不知所踪。尽管每天点灯熬油,我还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此时已经是十一月底了。09年的冬天特别冷。很早就下了雪。我的房子走风漏气的。棉被很薄,墙壁也很薄。我把能找出来的衣服都找出来穿。但还是很冷。我就每天在教室呆到尽量晚。教室的暖气很足。之后我在学校就再也没有见过陆路。他好像蒸发在脏兮兮的雪水里了。十二月初的时候D22有一个小演出。那天北京又下雪了,很冷。我就决定去D22喝点酒。到了D22我就哭了。当时在台上演出的乐队是我和陆路最后一次演出的时候排在我们后面的一个乐队。我忘了叫“水果糖”还是“水果硬糖”什么的。但是他们唱的那个歌我记得。我和陆路当时都觉得挺好听的。我不想让拿着认识的朋友看到我哭。于是我就急匆匆地躲进了厕所。这时候我看到了陆路。他苍白着一张脸拎着啤酒瓶在厕所门口的大沙发上坐着。我冻在那里。我冻死了。我还是站着,盯着他的脸看。这回他身边没有蛆,他也看到我。他看着我。然后喝了一口酒。我的眼泪被吓回去了。我说:“陆路。”我发现每一次我叫他的名字都显得温情脉脉。他往旁边挪了挪,我僵硬地坐在他的旁边。陆路举起手里的一个数码相机不停地看。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突然觉得很没意思。我想站起来走。这时候陆路拽住我,他给我看照片。我把头凑过去。看到了我们。那张照片不知道是谁照的,照得也很烂。我和陆路的眼睛都是红色的。我们坐在吧台上傻呵呵地笑着看镜头。一模一样的表情。可能当时我们的背后有光。你可以看到我们身上和毛孔里有金色的细微的光芒涌现出来。我被这照片感动了。陆路跟我说:“我老看这张照片。”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我浑身颤抖,痉挛一般拉住他的手。这时候我有一种降落的感觉。陆路走了以后我开始慢慢上升,升到空中我就开始被吹着飞。我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这样一种情绪尽管我自己不知道。直到我拉住他的手,重新坐到他旁边,并接触到他实在的躯体的时候我才降落。陆路问:“你觉得照片好么?”我说:“好。”他问了很多遍。我们就像两个弱智在那里旁若无人地重复这些无聊的对话。演出结束后D22涌进了很多的外国人。一下就变得很吵。我就跟陆路说:“回家吧。”他看了我一会儿,说:“好。”我其实一直有预感陆路要回来的。我在脑子里为自己设计了很多场景。我想陆路要求着我回来。然后我要在D22众目睽睽之下扇他一个响彻云霄的大巴掌。我想了好多场景,都跟这个很类似。但没想到我降落的时候如此软弱。不得不承认我当时小心翼翼。我生怕陆路跑了。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还是固执地拉着手。尽管我的手在北京冰冷的空气中已经没有了知觉。我还是怕放开手。我以前从不对陆路表现出我对他的需要,不表露爱,不拉手,就像两个细胞。但是他的出走着实吓着我了。我在手上悄悄地使劲。我每隔三分钟就神经质地叫一遍他的名字。我们两个曾经的疯子第一次平心静气地走在路上。那时候我觉得我们都老了。我们回到家后气氛有些尴尬了。我松开陆路的手。陆路回房间摸着蓝色金丝绒的窗帘说:“我回来过。夏天的时候我老是回来住。可是你一直没回来。最后我把窗帘换了,就走了。”我很冷并且有些烦躁。我搓着手说:“陆路,不是我不回来。我酒精中毒。我回家了。我差一点就要死在这个该死的地方。”陆路诧异地看着我。我对他做了一个很美式的耸肩。我们沉默了一会儿,陆路把他的琴拿出来摆弄。我又开始不对。我坐到陆路的身边,嘲讽地说:“陆路,你就像有多动症的小孩。你永远不专心。不管是跟我在一起还是跟你的正常人女朋友在一起。你都不认真。你真混蛋!”陆路停下手中的活计伤心地看着我。我有点后悔。我想陆路要是走了我该怎么办?他要是生气了我该怎么办?想到这里我闭上嘴。摆出一副矛盾的脸。陆路说:“你唱lulurun吧,我很久没有听到这歌了。”我拿出琴开始唱:假如真的存在万能的上帝他一定优越的偏执狂般地思考把爱压制成信息隔离开人们用悲剧性的法则撕裂每一颗心如果他真的存在我想去试着祈求给我一个保证让我一直在你身旁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并有亲吻你的力量用我不悠扬的歌声温暖你整个旅程lulurunlulurun以前我们总是合成出各种好玩的音色弹这首歌。这次我用的是最原始的钢琴音色。唱到最后我哭起来。陆路拿出一盒七星递给我。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爱抽七星,在七星还卖十块的时候,因为它颜色好看。有天空蓝和微风蓝。我们想有一天会出来海洋蓝。就是水立方的那种颜色。但现在我只抽双叶,因为便宜。我摇了摇头。陆路热切地问:“我们还是不是合作伙伴?”我说:“你越界了。”我是哭着说的。陆路黯然下来。那个时候我一点也不后悔,我想以后要是谁再跟我提什么他妈合作伙伴。我一定会杀了他。陆路晚上还是留下来了。我们一起呆了一周。站在的陆路跟以前那么的不一样。我以前总是说,他是一个完蛋的少年,他是死去的月亮,他是我的才华和全部的美丽。他变了。变得很容易伤心很软。他好像已经失去了把我瞬间杀死的能力。他甚至给我念诗。那是早晨,刚下了雪,天很晴。他坐在一个信箱上,我给他剪头发。他的头发像他一样,又软又伤心。陆路说:“我给你念首诗,海子写的《七月的大海》。”我记得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在七月我总能突然回到荒凉赶上最后一次我戴上帽子穿上泳衣安静的死亡在七月我总能突然回到荒凉他的头发扑簌簌的从我手中落下来。东边的太阳照射进来。我突然想,海子死的时候一定很美丽。陆路已经很少写歌。他开始写一些莫名其妙的诗。我问:“陆路,你站在为什么不唱歌?”陆路歪着头想了一会儿说:“我只是想试试别的疏通方式。写歌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方式。高中的时候我们班转来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生。我第一眼见她就想得到她。我想到她就会让我觉得特别幸福。后来她真的给了我,我觉得感觉很不错,但也没有多幸福。现在我已经可以写各种各样的歌。我觉得很不错。所以我想换一种方式。没别的。”在周五的时候我带着著名的陆路见了蓝精灵夫妇。他们开了一个houseparty,Arty也在。她看着我,又看看陆路,有点闷闷不乐。我走过去对他说:“这是陆路,他是我的爱人。”蓝精灵听我讲过无数著名陆路的事迹。他悄悄的把我拉到厨房说:“他可真陆路。”我笑了。晚上在回家的路上我跟陆路说:“我每次看到蓝精灵都很幸福。因为他沉浸在军军的爱里。”陆路扭过头对我说:“我也很幸福,我沉浸在你的爱里。”空气很湿润。我摸了摸那块颜色暧昧的蓝拨片。轻轻拉住了陆路的手。整个星期我跟陆路一起睡在我的房间里。因为能看到早晨的树和树上的喜鹊。每个早晨我醒来。陆路还在睡觉。我看到窗外微弱的日光,听到喜zhazhazha的声音。陆路就像死去一般紧紧抿着嘴唇。空气中飘荡着陆路温柔的药味。那些早晨我总能看到永恒。陆路跟我在一起的最后一天是年的元旦。我们一起在五道口的一家韩国的超市里买了两个蓝色的棒棒糖。吃得我们的舌头都变成了蓝颜色。我们兴致勃勃地带着两个蓝舌头去了mao参加元旦大party。太多人在了。大家都愿意写很多新年愿望投进箱子里。我们带了一瓶自己酿的酒,里面混合着伏特加,杜松子,桂花酿,二锅头,柠檬汁,菠萝汁,薄荷糖和安眠药。好像毒药一样的一瓶酒,被好多人传来传去。最后在木马的手里。木马喝了一口,说:“真好喝,像果汁一样。”我和陆路像刚认识的时候一样开心。我跑来跑去的,写了很多新年愿望。我写:我希望和陆路永远在一起。希望我们能把下辈子的房租都付了。陆路在迷幻的灯光下不知所措地笑着。有那么一刻我觉得他要离我远去了。他好像一片纸老虎,慢慢地飘到了屋顶上。但是他一笑,露出了他的蓝舌头,一切都真实了。年的元旦不冷。整个街道上都是欢天喜地的人们。我和陆路在半夜搀扶着回家。陆路说:“我们去天台坐会儿吧。”我们就跌跌撞撞顺着梯子往上爬。一边爬一边笑。我说:梯子怎么这么长啊。我爬都爬不完。”我的声音在楼道里显得特别大。楼下有一个人开了防盗门又愤怒的关上了。陆路把我拽上天台。树上的彩灯汇成河,街边的路灯汇成河。天空是一种奇妙的红色。我靠在西边的栏杆上唱lulurun。陆路慢慢地走到东边的栅栏旁边。他冲我笑。我也笑。看到他身后东方的天空开始有一种蓝色天鹅绒和红色天鹅绒混合的颜色。紫色的晨曦。他坐在栏杆上晃腿。我大声唱:“lulurun,run。”这时有一阵寒冷的晨风吹过来。我打了个哆嗦。陆路一如既往地笑着,他的头不停地向后仰,向后仰。最后,他整个的身体都仰在空中。就是在那一秒不到的瞬间,他翻下栏杆。我看着看着开始清醒起来。我清醒起来就尖叫。我发现东边栏杆上没有了陆路。哪里都没有陆路。叫:“陆路!”然后冲到栏杆旁边。往下看。陆路以一个奇怪的安详的姿势在水泥地上扭作一团。只有一个轮廓。但是陆路着陆了。我对我唯一的爱人陆路说的最后一句话是:“lulurun。”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hongguoxiaofua.com/tyxf/6482.html
- 上一篇文章: 新闻早七点2万元拾金不昧的好少年不见
- 下一篇文章: 震撼16岁少女全身92被烧伤,却鼓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