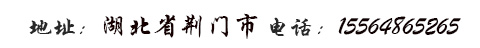写在毕业五年
|
庆国庆中科白癜风让您告白 http://m.39.net/news/a_9130637.html 今年是我毕业的第五年,来悉尼的第七年——从七月开始,悉尼将成为我生活过最久的城市。 年7月,在成都双流机场的国际航站楼里,我和父母拍了一张合照。照片里父母站在两侧,严肃的脸上带着隐约的担忧。我在他俩中间,歪着头,笑着露出了八颗牙齿。那时的我对未来毫无规划,只想出国看看,然后回国找份会计或银行的工作,过轻松的日子。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我试图探寻自己为什么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时,脑子里总会像电影般闪过一些片段。那些片段似乎都是出于偶然,但回头看时它们却被串联起来,指向今天我所在的位置。就好像乔布斯在那个著名的演讲里说的一样:「Youcantconnectthedotslookingforward,youcanonlyconnectthemlookingbackward.」(向前看时你无法将点连起来,你只有回头看时才能将它们连接起来。)——悉尼大学·摄于年6月28日—— 一 回忆起来,我总觉得一切都是从初中那节普通的英语课开始的。那似乎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天是成都惯有的阴天。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我的同桌是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儿。课间的时候我们刚用剪刀剪开并分吃了一颗英语老师发的巧克力。那个扎着马尾,眼睛又圆又大的年轻英语老师站在讲台边问我,「Edith,你最想去哪个国家?」我站起来,土黄色的冬季校服长长的袖子垂下来遮住了我的手。「澳大利亚」,我挠挠头说。我的头发很短,像个刺猬趴在头上。那时候我的英文名字是Edith,我在来悉尼时改掉了它。后来我问一个澳洲同事,Edith和Summer哪个更好。他说,「Trustme,Summerisagreatname.」(相信我,Summer是一个很棒的名字。)那一刻我觉得很高兴,因为多年后自己终于有能力选择——无论是英文名字还是生活的城市。这种类似「命中注定」感的另一个场景发生在大四。我和同专业的一个姑娘一起吃完午饭往宿舍走。走进丹青学园的时候时我说自己要去悉尼读研。姑娘挺吃惊的。她问我,「为什么要去澳洲啊,难道想移民?」「怎么可能,毕业就回来了」我回答得干脆。两年后,我被毕业的焦虑团团围住,却没想过离开悉尼。后来想到她那句话,总有些恍惚,好像那个午后的一切都被罩上了一层未卜先知的薄雾。——徒步偶遇蜥蜴·摄于年12月05日—— 二 年7月,毕业的慌乱伴随着悉尼冬天的第一股寒流席卷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在同期毕业的留学生里,一小部分优秀的人在没有绿卡的情况下就顺利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准备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大放异彩;另一小部分人坚定地回国发展;但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在毕业季的洪流里摇摆不定,挣扎求生。那段日子我常接到朋友的电话,通话内容永远围绕着回国、工作和绿卡。焦虑和惶恐的感觉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有时聊着聊着,对方的声音就带上了哭腔。那时的我在悉尼东区一家不足十人的会计师事务所实习。公司很小,却充斥着权利的争斗,复杂的办公室政治压的我喘不过气来。 事务所在Edgecliff火车站旁一栋白色楼房的第三层。白楼老旧的电梯停在三楼时总会沉重地发出“咣当”一声,并在几秒后伴随着“吱吱嘎嘎”的声音缓缓地开门。每次门打开前,我都会深吸一口气,然后俗套地对着电梯镜子里的自己说一句加油。和实习一同进行的是PTE的准备。PTE是类似雅思的英语考试。满分90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拿到79可以加20分。对于已经涨到75的绿卡获邀分数线来说,PTE至关重要。第一次考试前我和熟识的学姐在唐人街一家西安餐馆吃饭,学姐叉起热腾腾的炒面吃了一口,然后认真地看着我说:「我觉得你的口语可能会有点问题。」一向口语不错的我认为是学姐多虑,不以为然地咬了一口肉夹馍。但很快她的话得到应验,我的成绩出来,口语只有50。主要原因是发音太轻,机器不能完全识别。这是很多考过PTE的女生都遇到过的问题。在之后的两个月里,我按照网上的经验拼命练习腹式呼吸,将「机经」背得滚瓜烂熟,并在最疯狂的时候找了根绳子绑在腹部控制发音位置。在持续每天长达两三小时的练习之后,我再次参加了考试。第二天拿到成绩,口语30。——雨中的蜗牛·摄于年02月18日—— 三 因为毕业的焦虑以及工作和PTE考试的双重压力,我的食量大得惊人。下班回家的路上有一家肯德基,我常不受控制地进去买一份ZingerBox。一份ZingerBox里有一个汉堡、三块鸡翅、一个土豆泥、一份薯条,以及一听百事可乐。我可以在一顿饭里毫不费力地将它们全部吃光。在许多个华灯初上的傍晚,我都一手拎着肯德基的外带盒,一手拿着冰凉的可乐,迎着寒风匆匆地走在回出租屋的路上。在毕业的那几个月,我吃掉了比前半生加起来还要多的炸鸡和甜食。我的体重像吸水的海绵一样蹭蹭上涨,到了十月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衣柜里合身的裙子只剩下了一条。与此同时,我开始在夜里莫名其妙地以每小时一次的频率醒来,然后按开手机,干涩的眼睛麻木地看着屏幕上显示凌晨一点,两点,三点……一直到天亮。后来在和朋友聊天中我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经历过类似的状况——无处不在的焦虑感将睡眠夺走,我们如同马孔多的居民,一夜之间统统患上了失眠症。我很快放弃与失眠对抗,并开始早早起床出门跑步。那时住处对面是一个很大的公园,公园里有一座火车桥,桥洞里住着许多无家可归的人。有时我会在附近停下,看着那些远比我不幸的人们在晨光里起床、刷牙、整理床铺。后来我在一本叫作《无缘社会》的书里,读到过一个被称作石田君的流浪汉。那个刚过五十岁的日本男人在原公司干了二十年后因为公司效益下降而被迫离职,又在劳务派遣处工作一段时间,最后因不愿申领救济金而彻底失去经济来源,露宿街头。他告诉记者,「为了御寒,他每天夜晚都得不停地行走」。在那句话的后边,记者写道:「他的鞋尖已经破了,看得到变黑了的脚趾甲露在外头。」虽然如此,石田君的心里却依旧充满着希望。在勉强接受了记者请他吃的一顿饭后,他郑重其事地向记者鞠躬致谢,并说:「吃完这顿饭又有精神了,明天一定能找得到工作。请你们等我的消息吧。」——25岁生日公司老板送的花·摄于年03月08日—— 四 五年前刚毕业的我和朋友们,迫切地想要独立,不愿再领取父母的「救济金」,就像一个个石田君一样,背负压力却又满怀期待地在寒冷的夜里独自行走着。有一天家人打来电话劝我回国。言语温和,却难掩失望。研究生毕业,却没有正式的工作,也没有绿卡,甚至身边没有一个可以照顾自己的人。我有许多话堵在心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挂了电话,在床边坐了很久。在那年南半球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决定拍一个采访视频,并以这个形式回应父母的质疑。接受采访的朋友们在镜头前分享着毕业的烦恼和惶恐,但谈到拿绿卡时,几乎所有人的答案都是想试一试。其中一个姑娘语气温和却无比坚定地说道:「我不想当个逃兵。」虽然大家都知道回国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但是在那个特殊节点,离开却成了逃兵的代名词。如今看来,当时的执拗颇有些画地为牢的幼稚,但五年之后的今天我愿意将其视作命运。——偶遇蓝花楹和猫·摄于年11月12日——— 五 命运的道路在黑暗中盘桓良久后,终于开始通向光明。拍完视频后的几个月里,我和朋友们陆续考过了PTE,拿到了绿卡,也纷纷找到了能养活自己的工作,有的人甚至找到了生命的另一半,进入了人生的新篇章。年5月,绿卡获邀的我辞去了事务所给的全职工作,开始了间隔年。半年之后,我按照澳大利亚移民局的要求,从遥远的巴塞罗那飞回悉尼,第一次以永久居民的身份登陆澳洲。入境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接过我的中国护照,盖上入境的印章,然后笑眯眯地对我说:「Wel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hongguoxiaofua.com/szxfgmd/7758.html
- 上一篇文章: 最后一波学前教育小故事来袭10位骨干教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